又比如,要从形式主义、层层加码的一刀切防控,尽快转为法制化、人性化的居民自主、自发防控,全面禁止各地强令要求没有发病迹象、非密切接触者的外地旅行人员居家隔离14天的做法,提倡通过防控知识宣传、加大口罩等卫生用品供应力度等方式支持人民群众自发、自觉地进行疫情防控。
目前有些地方搞形式主义,表面上税是减了,但实质性没减多少,减与不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必须实质性减税。但是,民营经济创造的GDP占到60%,而银行贷给民营企业的贷款比重只占25%。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在与各民主党派协商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纲领。从全国信贷增量来看,2013年到2016年,国有企业的占比从37%增加到83%,而民营企业占比则从63%下降到17%。企业制度是关键,制度的创新会激发企业的活力。前几年黑龙江国有经济比重为64%,吉林56%,辽宁45%,占比都很高,包袱太重,活力不够。有几个数字强烈刺激了我:2016年美国财政年度,美国政府对外发出投资移民签证9974张,其中发给中国的投资移民签证7515张,比重高达75.35%。
也可以概括成八个字,即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比如去产能、去杠杆是有中央政策支持的,但有的地方在执行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有不一样的标准,我们不能戴着有色眼镜来落实政策。怎么实现它?当下投资界要注意,中央给出的扩大内需方针,强调了消费和投资,按我的理解,投资是关键的支撑力量,消费是由投资带动出来的潜力释放。
对应到轨道交通网各个节点上必要的停车位、停车场,可看一下最典型的平安大街,两边那么窄,那是原来的设计错误。但是如果从我们自己努力掌握好发展态势来说,尽力而为的应该是争取利用在原来下行过程中间已经在经济生活中间形成的结构调整、促进改革等带出来的一系列亮点,继续追求在速度重心有所下移以后,仍然完成这个L形的转变,对此我认为2020年就比较关键了。想一想,这个事情又是可以对接到PPP的,政府少量的钱进行补贴之后,可以带动一轮一轮的建设和百姓美好生活愿望的落地实现。这算是我说的书生之见,请大家指正。
领导人的说法是引领经济新常态,那么L型转换下面要拉出一个尾巴来,进入一个平台状态下面重点通过几个方面来讨论。

反对保6派认为,经济的潜在增速其实已经在6%以下,所以人为刺激保6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其次,软价值的实现是分段的实现,先有公众价值,后有盈利模式。其次,是重视流量的价值。软价值创造的三要素是有效研创、流量和体验。
从刚才三大需求来看,中国经济这一轮下滑,更多的是长期性的原因,而不是短周期的波动。外需减少的同时,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也下滑,其背后是两大长期不可逆转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四次传统工业革命的进程已经基本上结束了,现在中国经济进入到了快速工业化的后期。虽然全球供应链稳定性受到了一些冲击,但也许还会为国产替代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未必是靠逆周期的刺激政策能够解决的,更多要靠深化改革来恢复中长期的发展动力。
所谓软价值就是在商品当中的研发、创意、品牌的价值,那些低端的、消耗自然资源,污染环境、卖加工费、卖硬件的产品,未来在经济当中的比重会越来越低,而软价值的比重会越来越高。有了流量以后,才有产品——如今大众点评市值已经6000亿。

总之,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更多要以长期眼光去看待当前的经济问题,要推动深化改革,创造新红利,要把握经济增长不平衡性和新经济的软性特征,要掌握软价值创造和软价值实现的新规律。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很悲观?我个人也不很悲观,因为每一轮传统经济、传统产业受到严峻挑战的时候,往往也是一些新产业的爆发点,各方面的力量都会努力找到新的出路。
中国这一轮经济下行,是改革开放以来较长的一轮经济下行,大概从2007年一季度可以算起,到现在差不多13年了。这是未来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主要力量。90年代日本也经历过一次十年以上的经济下行周期。对于传统制造业而言,100%的投入应该都是有效投入。我们认为未来十年的时间,外需作用逐渐减少可能会一直保持这样的趋势,大约到2030年左右,中国将实现一个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平衡,也就是说制成品贸易顺差减少到零。到底应不应该保6%,关键取决于以下几个判断: 1)当前的经济下行到底是周期性的问题,还是长期性的问题。
沿着新需求路线,则要关注知识教育产业、文化娱乐产业、信息传媒产业、金融科技产业、新零售和健康养老这些高端服务业。第二,中国快速城镇化的阶段也差不多结束了,现在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0%,还有10%的空间。
不仅仅是总量问题,更多的是结构性的问题。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看一看过去四年的贸易顺差变化。
除此之外,一般的经济下行周期就是三五年。首先,软价值往往是非对称实现,阳光免费、星光收费,无论在支付软件,还是搜索引擎,几乎都是这样的价值实现路径。
对于软产业而言,90%的研发投入可能都是无效的,我们能不能接受研发和创意过程中的无效投入?又如何提高有效投入?这就需要我们从观念上,从人才结构上,从公司的组织架构上,从产品开发战略上,从激励机制考核办法上,要重新构建适合软价值创造的新公司管理机制。怎么样去创造流量,怎么样去导入流量,如何导出流量?这两天中国资本市场涨得最快的股票是叫网红经济的股票,实际上这是股市在挖掘流量的价值。一年前几乎是同样的时间,还是这个会场,我曾在这里做了一个演讲,题目好像是再造新红利。无论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公司,还是生物创新制药公司,他们的核心价值都不是他们的硬资产,而是他们的有效研创。
这次一个下行周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的问题,更多的是长期性的问题。1997年、1998年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形势比较严峻,但那个时候也是新浪、百度、京东、阿里巴巴、腾讯等新经济巨头的创立之年。
当前的产业结构,中国的制造业已经降低到占GDP的比重29.4%,将来这个比重还会降到28%、27%,甚至更低。这样才能顺应经济结构转型的趋势,创造更多的价值。
首先来看一下外需,外需离不开讨论中美贸易,虽然中美阶段性已经达成了协议,但是对未来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反复性还是不能低估,因为中美贸易矛盾的背后,是美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问题和美国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只有11.2%,美国制造业产品的逆差不是因为中国造成的,是因为他自己的经济结构造成的。其次,后发技术红利,作为经济增长根本驱动力也在递减,今后更多要靠自主创新。
3)到底需要逆周期调控政策,还是要更多地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的问题。2)到底是总量的问题,还是经济结构的问题。如果中国的快速工业化阶段结束了,快速城镇化阶段也结束了,那么与制造业投资、基本建设投资、房地产投资三大投资增速相关的产业都必须面对更多的长期转型挑战。当时我说一两年之内,我们的经济增速有跌破6%的风险。
如何提高有效研创,是所有的企业家和投资者都要思考的问题。沿着这个趋势下去,即便没有中美贸易争端的冲击,中国的外需对经济拉动的作用还会继续减少。
没想到短短的一年时间,就在不久前,要不要保6%,就已经成为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如果不能深化供给侧改革再造新红利,十年之内能稳定在4%这样的水平,就不错了。
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强国,但是未来在制造业领域,越来越多的价值应该是软价值。美国十年的经济增长只是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的增长,80%的人口并没有参与到增长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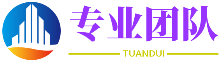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